在时代的脚步跨向二○一二年的前夕,摇滚乐队正为追随者筑起诺亚方舟,好莱坞灾难片被包装成洞见未来的启示录,书店里的心灵丛书更宣称蜕变重生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热切而无助地,整体人类社会共同簇拥着史无前例的集体焦虑。这是一个笼罩末日预言的时代,也是一个召唤马勒复活的时代。

二○一○年,马勒诞生一百五十周年;隔年(二○一一年),则是他的百年逝世纪念。短短几年间,马勒成为古典乐坛新焦点;从英国皇家亚伯特厅到澳洲雪梨歌剧院,从德国柏林爱乐厅到台湾国家音乐厅,马勒一个世纪之前所写下的恢弘乐章,就这样在世界各大殿堂轮番响起。
或许,末日预言并没有应验成真,但历经这么一阵彷徨、不安与失控之后,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天灾人祸纷传的生活环境、濒临崩溃边缘的政经局势、以及异常戒慎惶恐的集体潜意识。而此时此刻,马勒的音乐似乎带给世人格外深刻的解放和慰借。“我的时代终将来临!”这句话,曾经是马勒最为人所知的一句宣言,如今也成了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预言。
想进入马勒的心灵世界,就必须从他的诞生地开始探索起。一八六○年七月七日,马勒出生在克里希特(Kalischt),波西米亚境内的一个小农村,位于目前的捷克共和国,在当时则属奥匈帝国的辖地。几个月后,父亲伯恩哈德.马勒(Bernhard Mahler)带着一家大小迁移至距离数十公里之远的伊格劳(Iglau);一直到十五岁到维也纳求学之前,马勒绝大部分的童年岁月都在此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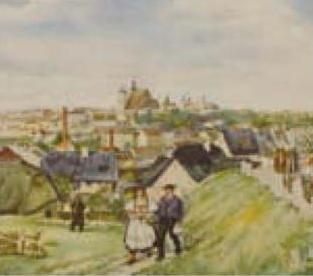
对于一个即将成为伟大作曲家的艺术灵魂来说,伊格劳无疑是一座充满迷人声响的城镇。不管是斯拉夫农民们的乡间舞蹈、行军队伍的号角声和振奋节奏,又或者茂密森林里的虫鸣、鸟啭以及呼啸传来的暴风雨声,都为马勒带来了鲜活难忘的听觉体验。这些新奇独特的声音记忆,就这样烙印于马勒的心底;日后,将在他的交响曲与歌曲当中,透过壮阔诗篇般的格局再次涌现。
伊格劳这座城镇为马勒带来了非常多重要的记忆与体验,但是身为一个诞生于波西米亚的犹太人,那一条切不断的民族情结却将跟着他一辈子。他曾经说:“对于奥地利来说,我是波西米亚人;对于德国来说,我是奥地利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我则是犹太人。不论哪一种身分,我总是被当成入侵者,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欢迎我。”来自国境之缘的马勒,不仅是自己口中的“三重游民”,似乎更注定是个永远颠沛流离的异乡人。
一八七五年,年仅十五岁的马勒独自前往维也纳接受专业音乐训练。那些年正值青春无敌的他,在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全面敞开了音乐与艺术的感官雷达,大量接触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华格纳(Richard Wagner)等前辈作曲家的作品,同时也对于视觉艺术、文学与哲学有着浓厚兴趣。每天穿梭在学校、图书馆、音乐厅之间,偶尔翘课溜到维也纳森林悠然漫步,十足是个充满抱负与梦想的浪漫文青。
马勒前后就读于维也纳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陆续以选修或旁听的方式接触了许多当时乐坛重要人物所讲授的课程,其中包括布拉姆斯派主力大将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的西方音乐史,以及华格纳派忠实拥护者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和声与对位。在布拉姆斯与华格纳两大对立阵营之间,马勒显然没有选边站,而是同时吸纳两方的音乐观点与风格;在日后的音乐创作与指挥选曲上,也可以很明显看出马勒对于两个派别的音乐家与作品都极为重视。
这段期间,除了广泛汲取音乐知识之外,马勒更开始尝试作曲,写了一些艺术歌曲、室内乐作品。第一部比较完整而大规模的作品,是一出名为《悲叹之歌》(Das klagende Lied)的清唱剧。虽然这部作品没有在维也纳乐坛引发太大关注,甚至还在乐友协会举办的“贝多芬大奖”比赛中挫败落选;但我们可以发现,马勒在维也纳精进深造的这阵子,他的作曲潜能已经逐渐在拓展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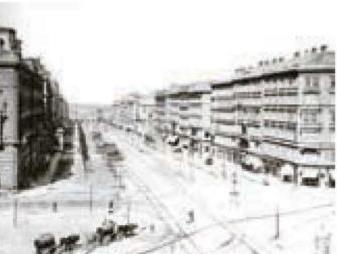
结束了维也纳的求学时光,马勒仍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一方面靠着担任钢琴家教谋生,另一方面也很积极地试图打开他的指挥家生涯。好不容易,在经纪人洛威(Gustav Löwy)的引荐之下,有些乡下乐团的指挥职缺找上门了。但这些工作机会在马勒看来,似乎就像许多年轻艺术家都必须面临的两难困境;生存与前途、经济与理想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运气。
马勒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些工作机会,不过从哈尔浴场(Bad Hall)夏天剧院、斯洛文尼亚莱巴赫(Laibach)剧院,一直到奥慕兹(Olmütz)市立剧院,他在接连三份指挥工作上都没有恋栈太久。其中绝大部分原因,想必是指挥家对于演出水平的期望,超出乐团的能力范围太多了。
然而,一旦马勒站在指挥台上,总能让台下观众惊艳注目。精准、高明的指挥魅力,也为他赢来卡塞尔(Kassel)普鲁士皇家剧院(Königlich Preussisches Theater)的工作。虽然少年马勒在此仍旧无法一展音乐抱负,但他和女高音乔安娜(Johanna Richter)一段从热恋到失恋的青涩体验,却让他留下甜蜜而伤痛的刻痕,以及一套令人心碎的连篇歌曲《流浪青年旅人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
不论歌曲或交响曲,马勒向来不吝于在音乐当中吐露他最私密的情感。正如同孟克(Edvard Munch)画笔下的《呐喊》,或者卡夫卡(Franz Kafka所描写的《变形记》,马勒也把他对生命的焦虑和挣扎统统写进了《流浪青年旅人之歌》。透过马勒多愁善感的灵魂,失恋的揪心之痛升华成动人歌调;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唯有感受到伤痛,才能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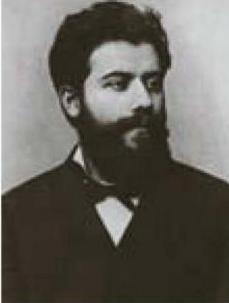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间,艺文界重要人士纷纷赶赴布达佩斯威嘉朵音乐厅(VigadóConcert Hall)。他们看着马勒步上指挥台,首先以凯鲁毕尼(Luigi Cherubini)的序曲作为开场,紧接着在一阵神秘深邃的声音中,开启一首五个乐章的“交响诗”。纵使上半部几个乐章之后,观众都给予鼓掌肯定,但是从“送葬进行曲”的乐章开始,大家纷纷传出不自在或者惊恐的反应。最后,乐曲结束于热情激昂的澎派尾声,但台下的观众却早已按捺不住情绪,众人稀疏的掌声之间甚至交杂着嘘声。

那一晚的演出失利,带给马勒非常巨大的打击。在后来的十年间,他不断地改写乐曲的结构与配置,不仅将交响诗的型式调整为四个乐章的交响曲,并且还加上了《巨人》(Titan)的标题,而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D大调第一号交响曲。
若要比起往后二十多年的马勒──或一九一三年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在巴黎造成骚动的《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这首《巨人》交响曲根本谈不上颠复传统或者惊世骇俗。然而,将哀悼与诙谐的风格大胆并置,对于当时的听众确实是一种极端的挑战;尤其在“送葬进行曲”当中,音乐色调游走于葬礼与狂欢节之间,更是让观众感到诧异与无所适从。
数百年来,古典音乐作品通常提炼自单一情绪,或者巧妙调和两种意念。可是马勒却试图在同一段乐曲里并置两种相互违逆的情感,不只呈现强烈的对比反差,也带出荒谬与讽刺的意味。在马勒的开创之下,更宽阔的人性层面融进了音乐当中;他的作品,是浪漫派的壮阔馀韵,亦是现代派的太初之光。诸多音乐家像是荀贝格(Arnold Schoenberg)、萧斯塔高维契(Dmitri Shostakovich),更前仆后继地追随他的典范,在不同领域拓展各自精彩的音乐突破。
世纪末的维也纳,空气中弥漫着安逸享乐的氛围。人们对于整体政经局势早已从无力变成无感,宁可沉浸美好的幻想世界,也不愿正视当下所处的现况。一八九七年,当维也纳市民还陶醉在小确幸当中,以画家克林姆(Gustav Klimt)为首的“分离派”(Secession),却突起划破了这片虚幻的和谐。他们企图带动视觉艺术、建筑和设计领域的觉醒与变革,主张艺术必须具备自由与时代精神。同一年,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与汉堡等地闯荡之后的马勒,也收到奥地利皇室谕令,回到了维也纳接任宫廷歌剧院(Wiener Hofoper)的艺术总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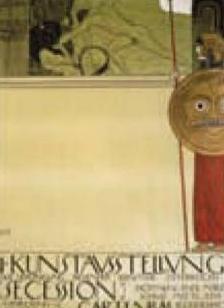
在维也纳的这黄金十年,是马勒音乐生涯的颠峰。除了不断有交响曲方面的创作,马勒也持续将诗集《少年魔号》(Des Knaben Wunderhorn)编写成歌曲,而马勒率领歌剧院的独特风格,以及他对于歌剧节目的策划与制作,在当时更是引起一阵风潮。
马勒相信:“传统,不是对灰烬的膜拜,而是火炬的传承。”马勒尊崇传统,却不受限传统。他请来分离派成员罗勒(Alfred Roller)为他设计舞台,并秉持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精神,让音乐、剧本、演出、灯光、舞台与服装设计等各个层面在歌剧舞台上完美统合。一丝不苟的精准掌控,加上前卫开创的呈现风格,无论莫札特、华格纳的经典剧目,或是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当代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