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相信:“传统,不是对灰烬的膜拜,而是火炬的传承。”马勒尊崇传统,却不受限传统。他请来分离派成员罗勒(Alfred Roller)为他设计舞台,并秉持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精神,让音乐、剧本、演出、灯光、舞台与服装设计等各个层面在歌剧舞台上完美统合。一丝不苟的精准掌控,加上前卫开创的呈现风格,无论莫札特、华格纳的经典剧目,或是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当代新作,都能在马勒的指挥棒下展现非凡格局。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当时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艺术总监的马勒应邀出席一场文化圈的社交晚宴。与会贵宾包括许多活跃于维也纳的艺文工作者,像是分离派大将克林姆、柏格剧院(Burgtheater)前任总监伯克哈德(Max Burckhard),以及风靡维也纳的气质美女爱尔玛(Alma Schindler)。马勒对爱尔玛一见倾心,整晚下来两人相谈甚欢、互有好感;到了宴会最后,马勒还邀请她隔天早上到歌剧院参观整装彩排,爱尔玛也欣然答应。

没想到才不过几周,马勒与爱尔玛开始密集通信和约会;整天都围绕在歌剧院工作的总监先生,终于享受到被甜蜜包围的滋味。隔年三月,马勒和爱尔玛闪电结婚,两个女儿普琪(Putzi)与古琪(Gucki)也在不久之后陆续诞生。事业、家庭两得意,这段日子大概是马勒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就像马勒的音乐那般悲欢交集,他和爱尔玛的婚姻关系也是时而柔顺、时而紧绷,后来爱尔玛甚至还出轨爱上了建筑师葛罗佩斯(Walter Gropius)。但在马勒心目当中,爱尔玛始终是他最无法取代的伴侣与知己,同时也是许多乐曲所要倾诉的对象。在第五号交响曲的柔板乐章,隐含了马勒对爱尔玛的绵绵情话;第八号交响曲如史诗般壮丽辉煌,马勒只将它“献给挚爱的妻子”;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手稿上,马勒更如是写着:“为你而生!为你而死!”(Für dich leben!Für dich sterben!)。
一九○八年夏天,马勒和爱尔玛来到奥地利与意大利边界附近的小镇托布拉赫(Toblach)渡假,他一方面享受这里的绝美景致,一方面也开始着手创作《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可是在那之前,马勒却经历了接连三次的命运重击:首先是年仅五岁的长女普琪死于猩红热,随后马勒又被医师诊断出有致命风险的心脏缺损问题,年底又因局势所逼而离开他具有十年革命情感的宫廷歌剧院。

似乎是意识到命运之神不再眷顾,此时的马勒对于生死的无常也变得格外敏感。他深恐自己也步上贝多芬、舒伯特(Franz Schubert)、布鲁克纳等前辈的后尘,在第“九”号交响曲后便辞别人世。于是,在完成第八号交响曲之后,马勒紧接着投入作曲的并非第九号交响曲,而是抒发他对大千世界百般眷恋的《大地之歌》。
从第三号交响曲开始,马勒几乎每年盛夏都会到乡间小屋写作新曲;奥地利的湖光山林,自然成为他触发灵感的丰饶宝库。到了《大地之歌》,马勒更因缘接触到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唯美诗篇,寄情山水的洒脱意境带给他偌大疗愈,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一种面对孤独与死亡的悠然豁达。马勒曾说:“当花草枯萎凋谢,大地只剩一片沙漠时,人们还是能透过我的交响曲知道大自然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或许青春短暂而生命也终将消逝,但音乐却能将美好永恒封存。
与死神僵持了数年之后,马勒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病逝维也纳,死于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心内膜炎。如同贝多芬过世时的雷雨交加,马勒也是在暴风雨之夜寂然挥别世界。五十一年的生命时光,马勒为全人类留下了九首交响曲、《大地之歌》等多部连篇歌曲,以及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马勒以空前绝后的巨人之姿,为交响曲的国度开拓崭新视野;不但创造了更壮阔的宏观格局,也探触了更深层的人性情感,让交响曲进化为一座足以容纳世界万象的无垠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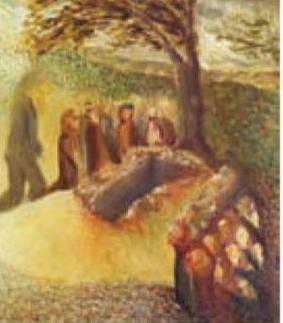
马勒一生的悲欢岁月终于结束,但并不表示他的时代已经来临。此时的欧洲,正掀起一波反犹太风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将在三年后爆发。纵使马勒早已在他的音乐里写下了爱与宽容,但这样的超脱与抚慰,毕竟不属于那个即将躁动的时代。
不过,无论马勒的时代是否来临,他的音乐永远都在未来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