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宗龙生来好动,喜欢挑战自己,在家里玩到落地窗的玻璃碎裂,弄得自己头破血流;母亲剪发,他玩刀片,玩到割掉半个手指。8岁时,母亲索性把他送去学舞,希望他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家住万华,父母卖鞋营生,10岁的小郑宗龙开始喜欢摆摊叫卖,“在街上,我妈不会管我,我要怎么叫就怎么叫,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街头像个表演的舞台。”那段日子真是开心,因为自由,也因此见到形形色色的叔叔、阿姨,“警察来追就很快乐,因为刺激的事要发生了。”
打工卖鞋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最后一次摆摊是在迪化街,一个喝醉的天字辈帮派分子突然打了我一下,又从旁边的日本料理店抢了一把长刀,在人群中追杀我。”刚排练结束的郑宗龙,体态略显疲倦,眼眸的光芒却没有消散,“被追杀很恐怖,但除此之外还有着荒谬。”看来理所当然、好端端的生活,倏忽之间,生死一线,这种突兀的荒谬也存在于念头,善恶同样可在一念之间。这荒谬或许也转译成他的舞蹈语言,当舞者的手势或身体正由内而外延展、线条即将优美完满时,却倏忽一个转折,顿时改变动向,打破了“理所当然”的美。
升学主义下,国中分为A、B段班,郑宗龙念的舞蹈班介于其中,但他往B段班靠拢。“下课时,班上的同学都在教室念书,只有我孤孤单单地出去玩,于是交了一些B段班的朋友,称兄道弟、义气相挺地一起吸安,也去勒索。”
考上北艺大之后的第3年,郑宗龙迷上和一群人打网咖。“那时学校排跳《薪传》,晚上10点一排完就杀到淡水网咖,打到早上6点又赶回学校练太极,就这样连续3天3夜不睡觉。”迷恋网咖侵扰了他的心思,“我不知道要继续跳舞还是做其他的事,甚至考虑过开一间网咖。”彷徨到了极点,他决定休学去当兵,却提早退伍,因为脊椎开刀,这一刀阻挡了舞者之路,但罗曼菲对他说:“你可以编舞。”那时,云门2创立不久。
团创立于1999年5月,由罗曼菲担任艺术总监。那年,郑宗龙因彷徨休学,同年9月,他与魔鬼交手,“一念之间,我做了一件坏事,做的那一刹那,921大地震就发生了,那是很大的天谴。”究竟是什么样的坏事?他守住这个私密,也与这深埋的黑影拉扯多年,今年云门2团满15岁之际,他接下了艺术总监职位,正为年度公演春斗编排新作《杜连魁》,“这支舞就是我的赎罪。”
王尔德的小说《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由台湾现代建筑大师王大闳译写为《杜连魁》,时代背景移至70年代的台北万华。故事中,贝席画下俊美的杜连魁,而杜连魁为了留住永久的青春与无限的热情而与魔鬼交易,他确实保有了俊美,但每做出一件悖德之事,画像中的他便逐渐老丑,终至倾颓败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这本小说是林怀民老师送我的,书中还附了两片CD有声书,但被我放在书桌上,一放就是5年,直到2012年我获得去纽约的奖助金才把它丢进行李。”郑宗龙走在纽约街头,紧贴的耳机里是有声书的叙述,借此练习英文听力,“刚开始时,我听不懂,但脑中的画面已经有人在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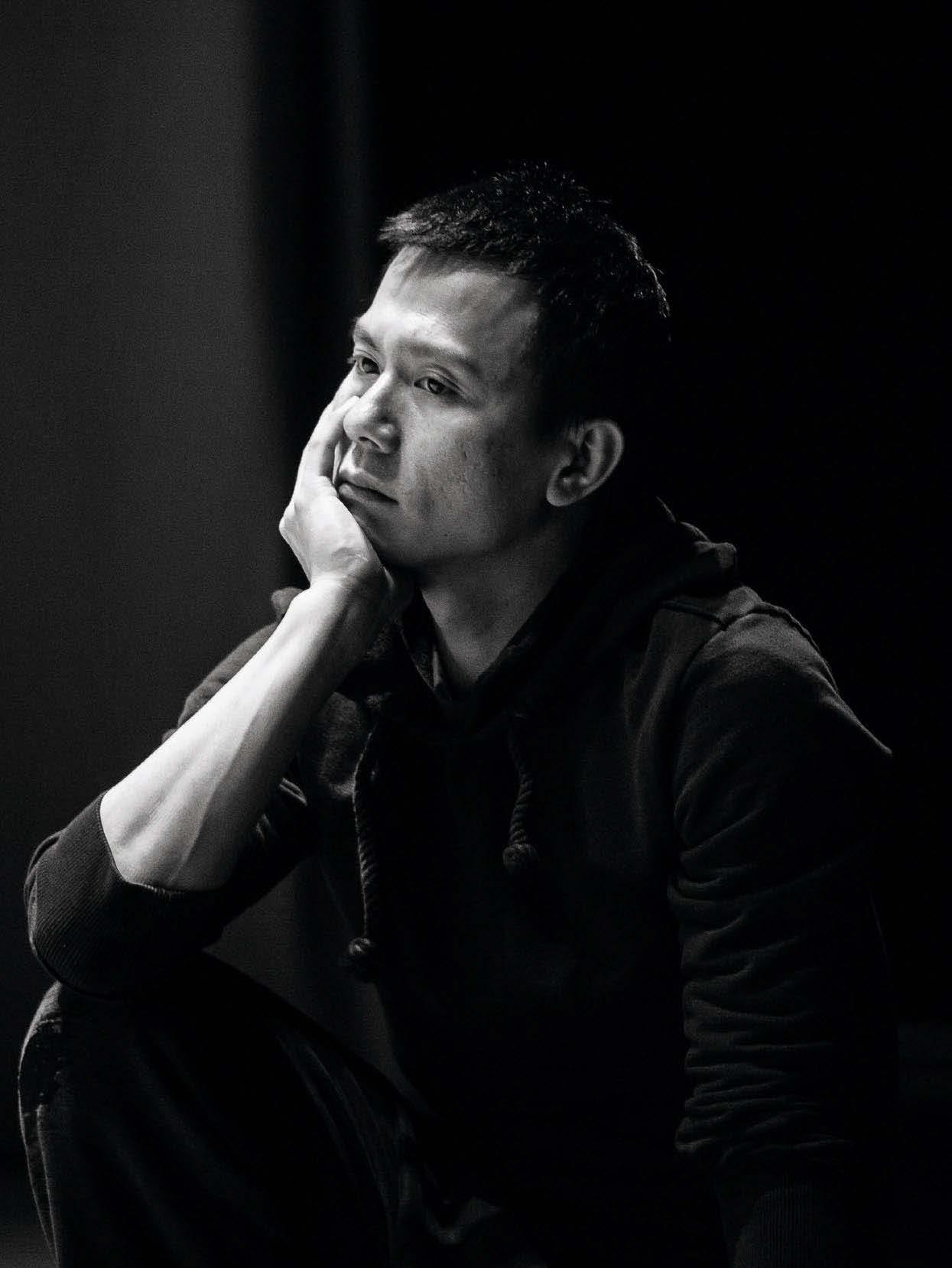
他查了字典,逐渐懂了故事,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故事中几个要角的影子,有着画家贝席的浪漫和理想,有时又像玩世不恭的吴腾以似是而非的话去影响他人,而杜连魁从一张白纸到逐渐沾染他人的黑影,积累成足以置人于死的黑暗力量,郑宗龙几乎有过同样的内在经历,或许杜连魁在舞台上自杀身亡,也是编舞者死过一回的替身。
舞作《杜连魁》中,舞蹈与有声书的叙述并存,“语言的逻辑与结构是以大脑去理解的,可是舞蹈是皮肤的,是视觉的,是感受的,让观众一下子用耳朵聆听,用脑袋去理解语言,一下子又用皮肤去感受舞作,两者如何切换?这是编舞的难处。”郑宗龙并加入北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表演的经验,小时候看的野台戏,开场便是使用北管音乐的扮仙,《杜连魁》也用了野台戏的结构,以北管开场,把整个人物介绍一次,再进入故事。”
过去的郑宗龙在舞作《墙》中,期待困缚可以被打破;《在路上》则希望有一条正向的路可以追寻、探索,在这出舞作赢得诸多国际奖项之后,他真的在美国独自开车一个月,走着精确而平稳的路,那时的他好想念曾取得“流浪者计划”而走向印度、喀什米尔的旅程,“那些人、那些火车班次,天天都有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每天都是新鲜的。但在美国,几公里会遇见什么,时速多少就会到达哪里,没有意外。”然而,一路从美国东岸开向西岸的过程,当他越过孤单的那道线之后,沿路的地貌、花鸟云朵、奇岩异石使他进入内在的宁静与透明。
“没有人会来拨弄你心中的那滩水,那真是喜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太近了,所以你的影子会落在我身上,我的影子会落在你身上,总有一些黑暗面会交叠着,互相作用。然而,美国那段旅程结束后,我接受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必然。编排《杜连魁》的过程中,我隐约感觉到在这支舞之后不会有路了,因为可以更自由。人生应该建构在每一个与人交错的当下,没有特定的道路必须追寻,而且我知道,过去那些丑陋、出轨、逞凶斗狠,不会再来困扰我了,那些曾被修补得乱七八糟的痛,不会再留下来了。”
或许在街上摆摊叫卖的开始,他便走上一条两端拉扯的路,路的一边是与人称兄道弟的义气与江湖习气,另一边是图书馆里干干净净、口齿清晰的学生,“我一直羨慕图书馆里那种彬彬有礼、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的人,也曾痛苦地练习变成那样的人。进了云门2团后,某次准备上台讲话,我在后台紧张得很,有人对我说:‘你做你自己就好啦!’我当场很没礼貌地回了一句:‘我极力想要从那个地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做我自己是要我回去那个地方吗?’然后我上台了,站得挺挺的,好好地说话。”
如今站上艺术总监这个平台,郑宗龙希望云门2团给出创作的空间再开放一点,只要是与身体的创作连结,无论是当代艺术或科技面向等其他艺术家皆可参与。“林怀民老师希望云门2团能在台湾各地跳舞,牵动更多人舞动身体。罗曼菲老师希望云门2团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进来跳舞、编舞。伍国柱说过,他害怕孤单,编舞可以让他和人在一起。而我,像在下跳棋,试图在这3者之间平衡地跳动。”
说起过往的心路,郑宗龙多次用到拉扯两个字,或许“挣扎”是彷徨的凌乱线条,而“拉扯”则是冲突的张力,后者更贴近舞蹈线条,透过《杜连魁》,他彷佛在两个拉扯的世界找到了和解之道。“不久之前,我梦见自己走在路上,一边是绿草地,另一边是荒地,中间有一条斜坡路,我看见妈妈迎面走来,没说一句话,想把钥匙交给我。”接下那把钥匙了吗?郑宗龙停顿一下,眼神迷蒙如梦,“我不知道,就在我妈妈想交给我钥匙时,画面就没有了。”
